备受关注的于欢故意伤害案,经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5月27日二审开庭审理,6月23日公开宣判,认定于欢系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予以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于欢案落下帷幕之际,对前段社会各界聚焦本案所关注的涉正当防卫的相关法理问题,有必要结合本案二审判决予以评析。
一、于欢的行为是否具有防卫的前提和性质
首先,于欢是否具有防卫的前提?本案一审判决认为当时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因而于欢持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前提,即否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的前提。一审判决的这一定性受到普遍质疑。
从刑法的相关规定看,正当防卫得以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有“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这种不法侵害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括一般违法行为。不法侵害应具有不法性、侵害性、紧迫性和现实性等四个特点。具体到于欢案,杜志浩等人为违法讨债所实施的严重侮辱、非法拘禁、轻微殴打等不法侵害,明显是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不法性;杜志浩等人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侵害了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具有明显的侵害性且持续存在。在此情况下,于欢为了制止不法侵害,对杜志浩等人实施反击行为可以减轻或者消除该不法侵害的威胁,理当具备正当防卫意义上的防卫前提。
其次,在于欢面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具有防卫前提的情况下,于欢的反击行为是否具备防卫的性质?依照我国正当防卫制度的法律和法理,防卫意图、防卫对象和防卫时间的认定是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的关键。
从防卫意图看,防卫意图是防卫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实践中,应遵循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进行分析和判断。首先,防卫认识是防卫意图的首要因素,是形成防卫目的的认识前提,具体是指行为人对不法侵害的存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不法侵害人、不法侵害的紧迫性、防卫的可行性及其可能的损害结果等有相应的认识。在于欢案中,于欢对正在进行的针对其母子的不法侵害有明确认识,即于欢认识到了自己及其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正受到严重不法侵害,其母子的人身安全也正受到严重威胁。其次,防卫目的是防卫意图的核心。所谓防卫目的,是指通过采取防卫措施制止不法侵害,以保护合法利益的意图和主观愿望。在于欢案中,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的行为,是希望以防卫手段制止不法侵害,是为了保护其母子的合法权益,即于欢主观上是出于保护自己及其母亲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心理态度,具有防卫的目的。概言之,无论是从防卫认识还是从防卫目的看,于欢都是具有防卫意图的。
从防卫时间看,于欢的行为是针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实施的。在于欢案中,杜志浩等人对于欢母子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没有因为民警出警而得到有效控制,当于欢母子急于随民警离开接待室时,杜志浩等人阻止于欢离开并对于欢实施了勒脖子、按肩膀、推搡等强制行为,杜志浩等人显然正处于实施不法侵害的过程之中,此时,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人,具备实施防卫的时间条件。这与事后报复是有本质区别的。
从防卫对象看,于欢是针对不法侵害人进行的反击。正当防卫的对象只能是不法侵害实施人。于欢案中,于欢持刀捅刺的对象包括杜志浩、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等四人。这四人均是非法拘禁、严重侮辱、轻微殴打等一项或多项不法侵害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是对于欢母子的共同不法侵害行为人,符合防卫的对象条件。在杜志浩等人共同实施的不法侵害中,所有不法侵害者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防卫对象不能局限于实施了最严重侮辱行为的杜志浩一人,其他共同实施不法侵害的行为人包括程学贺、严建军、郭彦刚,都可以作为防卫的对象。面对多人共同形成的不法侵害状态时,要求于欢只针对实施了最严重不法侵害的某一个人实施防卫,是不符合以防卫行为制止不法侵害的实际需要的。
于欢在防卫意图的支配下,在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过程中,针对不法侵害人实施反击行为,其行为当然具备防卫的性质。因此,本案二审判决纠正一审否定不法侵害存在、否定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的错误,认定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其行为具有防卫性质,是合乎本案事实,合乎法律情理的。
二、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
于欢的反击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这是本案一审后社会各界和法律学者关注与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本案二审中分歧较大的一个问题,存在系正当防卫、防卫过当、一般故意犯罪等三种主张。
根据刑法规定,防卫过当是指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行为。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了重大损害,使防卫由适当变成过当,由合法变成非法。因而从总体上说防卫过当也是一种非法侵害行为,防卫过当认定的关键在于对防卫限度条件的正确把握。
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通行的主张,在认定何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上,原则上应以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为标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在具体案件的判断中,行为人在确实具有防卫必要性的基础上实施防卫行为,如果防卫行为本身的强度与不法侵害强度基本相当,或者甚至小于不法侵害的强度,即使造成重大损害结果,也不能认为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如果防卫人采用强度较小的防卫行为就足以制止不法侵害,却采用了明显不必要的强度更大的行为,则应认定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总之,在何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上,主要是基于防卫方式、强度、手段不适当而认定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常见的情形包括防卫行为人攻击部位不适当、防卫工具不适当、因防卫方人数或体能优于侵害方情形下实施防卫行为等。“造成重大损害”意味着防卫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与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侵害相比明显失衡,一般仅限于造成人身重伤或死亡,不包括造成被害人轻伤或财产方面的损失。应当强调,防卫措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防卫结果造成重大损害这两个标准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
具体到于欢案中,依据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来衡量,于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防卫过当。在当时的行为环境下,针对杜志浩等人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为使其母子的人身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于欢可以采取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但杜志浩等人的主观目的是索要债务,他们的不法侵害手段相对克制,并未使用器械工具,也没有对于欢母子实施严重的致命性攻击或者暴力性伤害等行为,相比于杜志浩等人的侵害手段及程度,于欢使用致命性工具即刃长超过15厘米的单刃刀,捅刺杜志浩等人身体的要害部位,造成一死、二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其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明显不相适应,且造成了多人伤亡的“重大损害”后果,因而二审判决认定于欢的反击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是合乎法律规定的、正确的。
三、于欢的行为应否适用特殊防卫规定
在于欢案一审后的社会关注中,就有意见认为,于欢案可适用特殊防卫而免责;在于欢案二审中,于欢的辩护人亦提出本案可适用无限防卫(特殊防卫),二审检察机关出庭意见则认为于欢不具备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特殊防卫,即“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可见,特殊防卫的适用前提是防卫人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侵害人而实施防卫行为。实践中,正确适用特殊防卫条款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内涵和外延。从上述刑法规定来看,不仅其明确列举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是典型的暴力犯罪,而且其所使用的概括性词语“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也表明特殊防卫只能针对暴力犯罪实施。可见,一般的防卫行为既可针对暴力犯罪实施,也可针对非暴力犯罪甚至违法行为实施。但特殊防卫只能针对暴力犯罪实施,并且这种暴力犯罪并非指所有的暴力犯罪,而必须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这是刑法对特殊防卫适用前提条件的刚性规定。具体来说,第一,必须在发生了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时才能实施,对于没有危及到人身安全的犯罪,哪怕是暴力犯罪,如暴力毁坏财物的犯罪,也不允许进行特殊防卫,而只能进行一般防卫。第二,暴力犯罪侵害还要求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尽管不法侵害是针对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但侵害行为未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的,就只能进行一般防卫,而不能实施特殊防卫。有些犯罪例如侮辱罪可以是以暴力手段实施的,但是其属于较轻的暴力犯罪,对此即不能允许实施特殊防卫;若必须进行正当防卫的,也只能适用一般防卫的规定。在实践中,许多被认定为防卫过当的案件都是由于暴力犯罪的危害尚未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故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对暴力犯罪侵害,应根据具体案件中犯罪分子所实际使用的暴力是否达到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威胁程度来甄别,对于行为强度足以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则应当认为属于严重的暴力犯罪,可以实施特殊防卫。
就于欢案而言,虽然杜志浩等人对于欢母子实施了非法拘禁、严重侮辱、轻微暴力等违法犯罪行为,但这种不法侵害尚谈不上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一则杜志浩等人非法拘禁、严重侮辱等不法侵害行为,虽然侵犯了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合法权益,但并不具有危及于欢母子人身安全的性质;二则杜志浩等人的勒脖子、按肩膀、推搡等强制或者殴打行为,虽然让于欢母子的人身安全、身体健康权益遭受了侵害,但这种不法侵害只是轻微的暴力侵犯,既不是针对生命权的严重不法侵害,也不属于会发生重伤等严重侵害于欢母子重大身体健康权益的情形,因而不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侵害。综上,应当认为,杜志浩等人实施的多种不法侵害行为,虽然满足了可以实施一般防卫行为的前提条件,但因不属于“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不具有实施特殊防卫的前提,故于欢只能实施一般防卫行为,而不享有特殊防卫权,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免除其刑责。因而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并不存在适用特殊防卫的前提条件,也是于法有据的。
四、对于欢防卫过当行为的定罪处罚
关于防卫过当的罪过形式,我国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包括过失或间接故意两种心理态度,司法实务中多认定为间接故意,也有认定为过失或直接故意的。防卫过当罪过形式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案件定罪和处罚问题。根据二审查明的事实,于欢的行为应定性为防卫过当下的故意伤害致死的犯罪,对于欢造成两人重伤害宜定性为间接故意,对于欢造成杜志浩死亡宜定性为故意伤害而过失致人死亡。关于防卫过当构成犯罪的刑罚适用,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考虑到本案之过当行为造成一死二重伤的严重后果,对于欢不宜免除刑罚处罚,而以减轻处罚为妥。综合被害方先行的不法侵害情节恶劣以及于欢具有坦白交待犯罪事实、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对于欢可予以较大幅度的减轻处罚。因此,二审法院认定于欢的行为系防卫过当基础上构成的故意伤害罪,对其适用减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这是适当的,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总之,于欢案的二审判决以案件事实和证据为依据,以我国刑法的相关规范为准绳,切实贯彻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体现全面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从定罪到量刑均实事求是、合理合法地纠正一审的不当判决,其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并在审判程序上公正、公开,乃至向社会公开庭审活动,真正让人民群众在这起案件审判中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正义,使这起案件的审判成为了全社会所共享的法治公开课,从而成为一件典范性的司法裁判。
在线咨询
于欢案防卫过当法理问题简析
来源:网络作者:未知时间:2017-06-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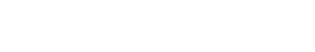
 浙公网安备 33038202002832号
浙公网安备 33038202002832号